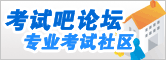· 2007年考研國家復試基本
· 2007年考研復試指南及各
· 調劑必備:2007碩士研究生
· 2007年考研國家線及全國
· 為招生單位免費發布2007
· 07年研究生入學考試初試
· 2007年考研政治試題及官
· 2007年研究生考試政治理
· 2007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入
· 2007年全國研究生入學考
· 2007年考研數學試題答案
· 2008年全國碩士研究生入
· 2007年研究生考試結束 4
· 2008年考研數學輔導系列
· 如何自我介紹--考研復試
· 2007年考研國家復試基本
· 2007年考研復試指南及各
· 2007年考研復試國家分數
· 調劑必備:2007碩士研究生
· 2007年考研國家線及全國
· 為招生單位免費發布2007
· 2007年研究生入學考試各
· 07年研究生入學考試初試
· 2007年考研政治試題及官
· 人大社提供:2007年考研
· 2007年研究生考試政治理
【參考譯文】
Ice-T:問題是否為社會責任…
(1)發行這本雜志的公司,怎么會制作出一張歌頌殺警察的唱片?
鋸短了我的霰彈槍
把我的車頭燈關上
我要幾顆子彈開花
我要轟掉幾個警察
死吧!死吧!豬!死吧!
(2)拉普歌手Ice-T的專輯《尸體清點》中的《殺警人》一曲,歌詞就是這樣。發行這張專輯的是華納兄弟唱片公司,屬于時代華納媒體與娛樂集團的一員。
(3) 時代華納公司的副總裁萊文投書《華爾街日報》讀者來函版說明公司的立場,文中提出兩點辯護。第一,Ice-T的《殺警人》被誤解了。“這首歌并不燃點或頌揚暴力,……而是他以虛構的方式嘗試進入一個人物的心靈……《殺警人》并不是呼吁別人槍殺警察,就好像老歌《弗朗基與約翰尼》并不號召被欺騙的戀人拿槍互射是一樣的。”我們不應該“設法讓表達訊息的人住口”,而應“仔細傾聽他訊息中的痛苦的吶喊。”
(4) 這種辯護是自我矛盾的。《弗朗基與約翰尼》并未假裝有什么政治“訊息”要人“仔細聽”。要說《殺警人》有什么訊息的話,那就是:殺警察是對于警察暴力正當的回應。而且不是為了自衛,而是隨便找個警察,有預謀的進行復仇行動。(“我知道你的家人在傷痛——Ⅹ他的。”)
(5) 殺警察是好事——這是歌詞里表示得清清楚楚的,不管是對黑人文化的“更全面的理解”也好,街頭的憤怒也罷,不論怎么解釋都改變不了這個事實,這和埃拉?菲茨杰拉德用歌曲說故事的情形不同。今天的熱門音樂常常如此:表演者與表演內容之間的分野被刻意模糊了。這首歌是政治宣傳,很時顯的是用來支持歌中表達的感覺的。特雷西? 馬羅(Ice-T)自己也說過:“我嚇唬到警察,警察也該被嚇一嚇。”這點應該是蠻清楚的。
(6) 時代華納公司對《殺警人》的第二點辯護是常見的言論自由論:“我們支持創作的自由。我們相信藝術家或新聞記者要表達的東西有沒有價值,并非取決于事先獲得政府官員或企業檢查人員的批準。”
(7)當然Ice-T有權說他愛說的話,可是這并不需要一家公司來為他提供一個講臺。而且公司選擇這個訊息來促銷,就不能以言論自由來推卸責任。判斷力并不是“檢查制度”。社會上太多“痛苦的吶喊”一直沒有人傾聽。這一個吶喊之所以被錄下來,被促銷,只因為公司旗下一個成功的藝人要錄它。賺錢沒有錯,可是公司不能拿了錢就不負責了。
(8)《時代雜志》的創辦人亨利?盧斯,如果聽說他的公司應該提供一個沒有價值標準的論壇來做意見交流,他一定會嗤之以鼻。在盧斯的制度下,編輯應該要做價值判斷,同時宣揚他們眼中的真理。《時代雜志》離開盧斯時代的僵硬作風已經很遠了——遠到能容許像這一篇唱反調的評論出現。這種進化是好事,可是不能用它作為很好用的借口來拋棄所有的標準。
(9) 公司企業當然不需要對獲得公司授權而出現的每一個字都同意。如果時代華納公司現在打算做“一支全球性的生力軍,鼓勵不同意見互相交鋒”,這當然很好。可是允許不同觀念并存的政策,并不是一張道德通行證。全國性醫療保健的利弊辯論是一回事,殺警察的利弊又是一回事。
(10)時代華納公司也頗值得同情。它的確是“一支全球性的生力軍”,媒體的觸角遍及全世界。如果它由上往下冠上嚴格的價值標準,就會被批評為公司檢查言論。如果沒有要求標準,也會被批評為不負道德責任。這是兩難的局面。可是在決定要做一股全球勢力之先就該有人想過這個局面。
(11)另外還有一個無解的兩難。不論《殺警人》本身的真實價值如何,如果時代華納公司現在收回這張專輯,會被視為向外界壓力屈服。這對全球性的集團來說是災難性的先例。
(12)1989年時代公司與華納公司的合并原意是要產生企業的倍數效果:整體的力量應該超過各部分的總和。《殺警人》引起的爭議可說是負面倍數效果的實例。消費者對《殺警人》感到惱火,于是開始抵制電影《蝙蝠俠續集》。有一位評論家如此“贊揚”《殺警人》:“特雷西? 馬羅的詩歌拿出彈簧刀,熟練地切斷生命的頸動脈”云云。《時代雜志》也不僅被批評為愚蠢而已,甚至被稱為腐敗。資深的時代華納公司主管們因為公司的產品而飽受攻擊,他們還得為這些產品辯解——這些產品其實他們根本沒有興趣,也并不真正了解;而且,在爭議爆發之前,肯定是根本不知道有這些產品存在。
(13) 無論如何,把《殺警人》當作“不同觀念的交鋒”來討論——甚至當作貧民區真正痛苦的、憤怒的吶喊來討論——本身就很荒謬。《殺警人》只是一項虛偽的商業制品,設計來以暴力影像刺激聽眾。它只是利用貧民區真實的痛苦來做進一步的刺激。特雷西?馬羅是為了幾個錢在做生意,和時代華納公司沒什么不同。《殺警人》對白人體制開了一個大玩笑,笑話中的笑點就是時代華納公司痛苦的辯白:“我們為什么不去聽聽拉普音樂要告訴我們的訊息?”
更多資料請訪問:考試吧考研欄目